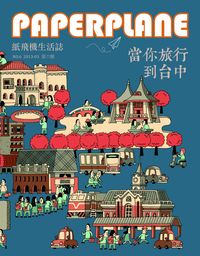一个人的时光
发表时间:2016-07-10 点阅:3208
其实,我是在极为慌忙的情况下租到这间宿舍的。
那时我南下古都攻读学位,一周只停留两夜。那是一座对我而言十分陌生的城市,我在此无亲无故,没有任何可供我借宿的地方,只得租房。
大学附近宿舍租金昂贵,我一个穷学生预算有限且只住两晚,那金额实在不是我所能负担,但眼看开学即在,住的问题若不搞定,落个露宿街头的惨况,我这个书也未免读得太凄凉了。
就在我买好睡袋做好最坏打算的那天夜里,好友P寄了封租房讯息给我,地点就在我就读学校的后方,包水包电包网路,不需押金,月租与我的预算相符。在这种地段开这种条件,魔幻的非常不写实,我心想,这若不是间凶宅,那肯定也是间鬼屋。
那是座五层楼的老旧公寓,藏在一条陋巷中,两旁满是随意停放的机车与脚踏车,房东是一对老夫妇,话少但十分和蔼,打过招呼后,两夫妇打开斑驳的红色铁门,准备领着我去看房间。
「住四楼没禁忌吧?」在昏暗的楼梯间,房东太太突然转头问了我这么一句,我摇摇头回应,房东太太一面缓步踏着楼梯,一面喃喃自语:「我是惊四楼不吉祥,你会‧‧‧」。
「会怎样?请你把话说完!」在那弥漫着霉味、古旧、昏暗的楼梯间,我硬是压下了这句已经到了喉咙的问句。
就学生宿舍而言,这里真的太安静了,除了窗外东宁路上来往车辆的呼啸声外,没有其他的声音。在这座老公寓中,没有监视器,没有先进的感应式大门,一层楼四间房,共用一套卫浴,铺的都还是二、三十年前才会有的那种蓝白相间的小马赛克磁砖,没有莲蓬头,只有一个洗手台与四个水龙头,没有天然气,瓦斯用完了,各楼层得自己叫,房间出乎意料格局方正且干净,除了一张床,一个衣柜及一张堪称破旧的书桌,甚么都没有,极简的风格,正合我意,没有任何考虑就决定租下,开始我在异乡每周两夜的一个人的生活。
在这老旧公寓住了一年半,我不曾见过与我同住一楼层的房客,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确存在。我对房应该住着一对情侣,房们的鞋柜放著几双男鞋和女鞋。左边与我一墙之隔的房客,应该是个男大生,他总是在晚上七点左右,走进浴室内洗澡,至于斜对房的住客,应该是个电影迷,房门上的电影海报,频繁的更换。
虽然我们不曾打过照面,但也不是没有接触,当我们楼层瓦斯用尽时,就会有个信封从门缝里塞进来,上面写着瓦斯费149元,请把钱装进信封后,塞进左边第一间或右边第二间,这是我们楼层的默契,用一种古老且不打扰的方式,默默进行着某种交流。直到我离开那栋古旧的公寓,我都不曾见过我的楼友们,那层楼,总是十分安静。
那是一段特殊的经历。我在古都待的时间并不长,除了上课之外,对这个城市其实没有太多记忆,唯独在那个房间内的某些时光,一直印象深刻,我猜想也许是因为在那房间里,我全然的独处,像包在茧里的蛹,纯粹的一个人在里面蠕动着。
正午时分,书桌前的窗帘挡不住光,房间内会垄罩着一层亮黄,那时的我通常桌上会放著一盒三宝饭,在路口港式烧腊店买的便当,老板娘是个没耐性的轻熟女,像电影《食神》里的「鸡姐」,嗓门极大,常操著带着香港口音的中文一边凶顾客(要画单啊,不然我怎么记得住你点甚么啊!),一边骂师傅老公(客人点三宝,你只切烧腊,耳朵聋了啊!)。
在那个午餐的时刻里,我一边挖著三宝饭,一边望着窗帘发呆,出神像个失智的老人,那房间太安静、太单纯,隔绝了所有的连结,仿佛一些简单的动作就足以回应整个世界。
光在我床边的墙壁上爬行,早已龟裂的墙壁承受不了如此密麻的步伐,而一块块脱落,激起阵阵尘烟。在那绝对的一个人的孤独里,意念得以有机的蔓延,不再修剪与捕捉时间,带着好奇想看看,这样的栽种会在我的灵魂中生长出甚么东西来?
会是自由吗?
如果不是因为生活所需,农夫们也许只想静静的坐在那一片绿色的田园里,听着风的声音。
会是自由吗?
我在时间无缝的流动里,敲下几个空白键,是否就可以凿出一个将自己掩埋起来的空洞呢?
脱轨,在一个人的时光里,我偷偷的叛逆。
一个人缩在墙角无所事事,逃离世界的喧闹。
那个时刻很安静,像是在梵谷的星空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