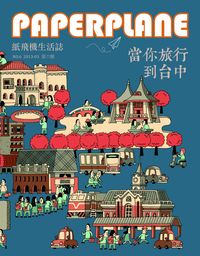夜的奏鸣曲(三)
发表时间:2016-10-24 点阅:943
05
人不多,整辆车除了轰轰的引擎声,没有别的声响,乘客们多往窗外望,用着自己专属的焦距失神。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,思绪跟着车子行进的速度发散,要不是她小姐粗粗鲁鲁的坐上我旁边的位置,我都没意识到公车靠了站。
她的行李不小,一句招呼也没打的硬是塞到了我脚边,我当下有些不悦,正准备开口请她移开行李时,她已经抱着自己蓝色的帆布包睡着了,公车离站才没多久,便整个人倒枕在我肩头上,熟睡像是整个世纪都未曾入眠一般。
我实在不太善于处理这种尴尬场景,我该戳戳她的手臂,叫醒她,要她躺到别处去?还是耸耸肩,礼貌性的暗示她,这样的睡姿让我有些困扰?冷气吹拂她的头发,微微的飘动,像一种轻柔的抚摸,发香、鼻息、体温,一瞬间我陷落在某种奇异的幸福感里。后来我什么都没做,假装没事的保持现状。
过了很久之后,我常常回想起那个瞬间,思索著那奇异的幸福感究竟因何而生?
因为寂寞,我想。为了避免碰触而将内在某种感知关闭而造成的空白之感。
那时的小绿就这样枕在我肩头上睡着,那是我们第一次的接触,以一种意外的亲暱。
我忍不住开始打量这大喇喇的女孩,心里有股冲动想多了解她一点什么。她的长发盖住了她的脸,但我仍可从发隙,看到她的脸,是个漂亮女孩呢,我心想,这也算是一种艳遇吧,一个女孩像猫一样枕在你身上睡着了。
她白色的T-Shirt上的确也印着一只带着墨镜的小猫,镜片上镶满了黑色的亮片,做工精致,下半身则穿着一件割满破洞的牛仔短裤,那些破口的位置十分微妙,有一种引人目光的黑色魔法。但真正让人遐想的,是她微开的领口,倾斜的身躯,让她露出了胸罩前缘的白色蕾丝,女孩的绝对领域,就在我眼前若隐若现。
我必须承认,把眼睛从她身上转开,需要一点决心,以及很多的道德谴责,那毕竟是对很多男人而言,极具吸引力的风景,只是非常的失礼,最终我还是将眼神转向了窗外,继续随着移动的城市放空,不是因为自己多么正人君子,而是作贼心虚的害怕自己内在邪恶的欲念被旁人发现。
我也曾偷偷窥视C的胸,小巧的胸衣,托衬著C精致的胸型,那肯定是数学家眼中最完美的弧线,没有任何公式可以定义它勾引欲望的强度,它的美感,只能在当下感受,视线凝结,意乱神迷,绝无仅有的审美经验,每一次的窥视,都带来不同的迷幻,交杂着欣喜、确幸与纠结的情欲。我不知道C是否知道我这小小的邪恶举动,说话时,她总是盯着我的眼睛看,像是在确认什么,也像在寻找什么,而我总会分心,不管是她身上飘散的沐浴乳香气,衣服上残留的洗衣精味道,饱满的耳垂,或是纤细的手指,都是我想探索的细节,这要是被C知道了,她肯定会生气。
这熟睡的女孩若知道她倒在一个已经许久无眠的男孩肩上,不知会做何感想。怎么会有人睡不着呢?或许她会这样问。说的也是,我似乎搭上了一辆只有睡眠的公车,环顾周遭的乘客,似乎每个人都闭着眼睛,身体无意识地随着车身晃动。入眠,是一种逃离世界的方式,特别是当你处在一个「只能如此」的时间或空间中,睡意特别容易来袭,像是生命的某个保护装置,截断虚无,用另一种虚无建构诡异的存在。
C曾对我说过一个梦,她梦见自己揹著笨重的登山背包,跟着两个看不清脸庞的男人,艰困的走在一条布满障碍物的小山道,梦中的她必须小心自己的步伐,因为一个失足,就会跌落山谷。这条山道极其难行,她必须不断地攀爬挡在眼前的巨石,每回她抬头,那两个只有影子般的神秘男人,早已站在巨石上,不知是等候她还是嘲弄她,C说在那场不断重复的梦中,她每次都会感受到一种极为真实的不耐,她不知道为何她要走在这条路上,只知道她无法回头,而那条山路无止无尽,仿佛做一辈子梦都走不完,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。C说,每次她从这梦境中醒来,都有一种解脱的喜悦。
我忘了我当时如何回应她,应该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屁话,我想我当时根本没有认真的听,那只是一场梦,无关紧要的梦。那时我口袋里藏着准备送她的礼物,一只铜制猫头鹰手环,我等不及想看C感动又惊讶的神情。那是C最爱的动物,我虽没亲眼见过,但C曾说过,她房间里蒐藏了一整柜子猫头鹰相关物件,她还曾努力说服家人让她养一只真的猫头鹰,只是最后没有成功。
那时的我,不会想到,C的梦,其实是个隐喻,我应该对她说:「每个人都这样活着,看不到终点啊,我们只能一直走着,一直走着,直到你失去希望,失去期盼,失去想像,只有到那看似绝望的时刻,恶梦才不会是恶梦。」
亲爱的C,昨晚我打开小房间内唯一的对外窗,惊见一只猫头鹰就站在我的窗櫺上。都市里哪来的猫头鹰?牠两颗正圆形的大眼睛,与我交接直视,偶尔用不可思议的角度转头随意张望。牠是夜里不寐的鸟,我是夜里无眠的幽魂,或许有着共同的气质与心事,因此牠并未被我惊飞。亲爱的C,我的世界里,处处有你的存在,尽管我是如此地想要将你从记忆中抹除。
回忆是另一种梦的形式,只是我仍醒著。
肩头上的女孩仍然熟睡,此时我看到公车偏离了车道,一阵巨大的冲击,惊醒了睡眠的公车,司机把车开上了安全岛,撞击力把一群乘客甩飞出去,微胖的中年妇人、西装笔挺的保险业务、大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孩、穿着套装的银行OL、要去医院看病拿药的老先生,在车上跌成一团。
我本能的用手护住身旁熟睡的女孩,但冲击力实在太大,她的身体带着我的手直接撞上了前座椅背,我的手发出一阵剧痛,大梦初醒的女孩,双眼迷濛的盯着我,接着抚著胸口,哭泣了起来。
在医院急诊室等待X光片的空档,女孩对我说,她叫小绿。
值班医生,看起来很年轻,蓬头散发,穿着拖鞋,有着很重的黑眼圈,拿着我们俩的X光片,对着日光灯看了一眼,然后转头对小绿说:「你该感谢你的男朋友,要不是他的牺牲奉献,以这种撞击力,少说断两根肋骨,没事,肋骨轻微挫伤,休养一阵子就好。」接着转头对我说:「这两根,你帮她断了,桡骨、尺骨骨折,等会就开刀帮你接起来。」
我不是她的男朋友,话都还没说出口,黑眼圈值班医生就一阵风似走掉了。
我苦着脸望向小绿,手实在痛得难受,她有点愧疚地对我说了声谢谢。
不久,我就被推入了手术室,睡了一场几年来最安稳的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