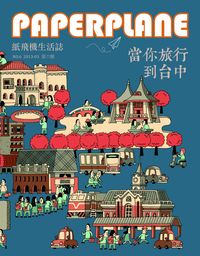在死亡面前思考真实
发表时间:2018-06-27 点阅:8722
门诊位于医院地下三楼,我找不到路,服务台的志工妈妈手指著安全门,要我走楼梯下去,很寂寞的一条路,灯光很暗,回音很大,耳里听到的都是自己颇为沉重的脚步声。走到地下三楼,推开厚重的安全门,出去是一条长长的廊道,左边是往停车场,右转往放射肿瘤科。
看着科室的招牌,老实说,我没想过那么年轻就有机会来这里挂号。
跟楼上开放式的诊间不同,这里明显刻意设计过,候诊室很宽敞,灯光是柔和的鹅黄色,或许是来得早,二十多张椅子只坐我一人,交了健保卡,护士招呼我量身高体重,这一个月,我又胖了两公斤。
等待叫号的时间,我四处走动,读著墙上最新高科技治疗仪器的介绍--锐速刀 (RapidArc),肺癌治疗最新科技,采用最新型直线加速器,进行360度全体积弧形放射治疗,比固定角度治疗更能保护正常组织,2分钟即可完成治疗......。
边看心里边想着,会不会以后我就得躺在那上面,让机器对着我转一圈,又或者,也许不只一圈。
「会不会睡不着觉?」这是医生开口问我的第一句话。
满头白发,莫约六十多岁,说起话来有个香港口音,像我常去的那家烧腊店老板讲话的腔调;声音很轻柔,细细的,听起来像是有些害羞,总之很温柔和蔼。
「不会」,我说。最近反而睡得比以前早。
翻着我带去的健检报告,医生盯着那串红字:「肿瘤指数异常」,看了我一眼,继续前翻后翻,试着从报告中的其他指数找出什么关联性的线索。
「cyfra 21-1」(细胞角质蛋白片段)指数超标,这个检查,主要应用于肺癌的诊断与监控,根据医学文献纪载,这指数有47%至61%的敏感度,及95%的特异性,简单说,根据这个数值,我最高有六成得病的可能性,虽然在科学上,这样的检测准确度仅有参考价值,但却足以吓坏每个数值异常的人,例如我!
「胸部X光呢?有没有异常?」医生问!
报告上打着「无明显异常」,我指著X光检测的结果给医生看。
白发医生点点头,用着轻轻细细的声音,略带安慰的说:「这样你可以稍为安心一点,80%的问题,Xray都照得出来,我们再做些检查,看看其他20%有没有问题,这些指数都是连动性的,单一结果不代表什么,我们先验个血,验个尿,如果没问题,你就不必担心了,下周我们看报告。」
谢过医生,拿了验血的单子,正要走出门前,医生像是想到什么,对我说:「先别想太多,记得要好好睡,减少肿瘤成长的因素!」我转头看了医生,他对我微微笑,老实说,是一个很令人安心的长者,但他的这句提醒,让我心里很沉。
我很想知道他心里的盘算和预测究竟是什么?他是怎么看待我这个拿着健检报告来求助他的年轻人?会不会他心里正想着:可惜了,还这么年轻,家人小孩该怎么办?又或者,他早已看过太多生死,看过太多切片,看过太多肿瘤吞噬病人身体与灵魂的景象、看过太多病人的离世,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些场景。会不会他的笑容与温柔,其实是一种同情,是一种无能为力下仅能给予的恩慈?
我转身离开。
突然之间,我什么答案都不想知道。
虽然只是健检报告上一个打着红字的指数,但却让我有一种即将面对死亡的巨大现实感,有些怅然,有点陌生,像见着了一位从未谋面的网友,有种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尴尬。不是恐惧,也不是不恐惧,「诡异的荒谬」可能是更精准的形容:如果下周白发和蔼的医生收起笑容对我说声遗憾,然后呢?就这样结束了吗?我的一生!
那有什么意义呢?我的一生!
戴上安全帽,发动机车,我脑袋中突然浮起了一些画面:女儿会不会站在我凌乱的书房哭泣,那张黑色的大椅子上,曾经坐着他的父亲?她才十二岁,可能无法再继续学跳舞、学英文,没有人可以让她无条件的任性。六岁的儿子,知不知道他的父亲再也无法陪他打打闹闹,幼稚的在下雨天的街道上踏水洼?而我的妻该会如何困顿辛苦的面对未来的日子?无论怎么想像,都没有好结局。我发现我留下的东西太少,不足以抵抗死亡带来的后果。
死亡在我原本的想像中,是个无梦之眠,一种永恒的绝对空洞,一切烟消云散的虚无,但其实不是,死亡对现在的我而言,将是生者汩汩不绝的哀伤。
这一刻,我才真的开始害怕,身体不自觉的颤抖起来。
在这一切混沌未明若有似无的惶惶时刻里,我认真地将死亡的可能性,写入我的生命日程中,然后,一切都变得不一样。
死之将至,放大了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意识刻度,从年到月,从月到日,从日到时,从时到分,从分到秒,从毫秒到微秒......。
然后,我看到了更多生命虚伪的表象,认知到我们留下太少真实的本质--那种尽管知道自己即将消逝,却也不觉遗憾,真真切切,绝不虚假的一些什么。
我知道人生充满了试炼,那些一次次努力冲撞与突破,以为成就了自己一些什么可以拿来跟朋友喝咖啡时说说嘴的事,其实常常过了就没了,像个美丽的烟火,引爆后仅有飘在空气中的硝烟,我其实常常想,这些我们以为的试炼,会不会都只是一次次的自我欺骗?到底什么才会是永恒的真实之所,如果生命如此短暂如此无常,我们到底得推开哪扇门,才不会留有遗憾?
在等待复诊结果的这些天,只要对着镜子,我便会问自己:是否成为了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?又或者,活了大半辈子,到头来却活成了自己厌恶的那种人?我是否曾做过一件真真实实改变世界的事?我是否不计毁誉代价坚持成就一个完整的自己?
越想心越慌,一辈子看似很长,却可能只是一事无成。
那些汲汲营营,到头来也只是生活的庸碌,不如一只生来只为了自由飞翔的蝴蝶。
死者之眠已无梦,然生者梦之,或许只有那些可以入生者之梦的,才是在死亡面前最真切的事--你曾在这世界烙下的某些印记,在生者心上刻下的一些痕迹,会随着地球自转、随着心跳的节奏,被想起,被感受的那些事。
有吗?我有做到这些事吗?
对着镜中的自己,我无比的哀伤!
一周过去,同样的早晨,同样的时间,这次我熟门熟路,推开安全门,顺着弯弯曲曲回声很大的楼梯走下,推开厚重的铁门,右转,沿着空荡的长廊,再次踏进放射肿瘤科门诊。我拿出健保卡,交给诊间的护士,她脱口问:「你要干嘛?」以为我是某个跑错诊间的糊涂病患,「看报告」我说,她眼中闪过一丝遗憾。
不同上次空荡的诊间,这次有个莫约五十多岁的大叔病患,她拿给护士的不是健保卡,而是一本看似重大伤病的小册子,封面上贴著条码。大叔颇有病容,很瘦弱,但却顶了个不符身材的大肚子,他身上的一切,彷若都失了控制,他看了我一眼,不带任何表情,空空洞洞。
我们都有可能遭遇这些总在自己人生想像外的鸟事,那都是些被抽干希望的现实,一如大叔空洞的眼神。那些意外,其实不算意外,只是一些被我们刻意忽略、遗忘的情境,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控制着某些事,但其实,我们只是避而不谈那些本有的真实,又或者说,我们习惯在虚幻的假象中存在。
因为真实无法编造,但虚假可以。
护士领着我再量了一次体重,一周内竟瘦了将近两公斤。
没有等太久,护士叫唤了我的名字,推开门,医生望了我一眼,请我坐下。
「肿瘤指数一切正常,别担心!」医生笑着说!
深深呼了一口气,放下一颗吊了半个月的心。
「只是你的血球面积小,带氧能力差,爬山要特别注意高山症,你爬山吗?」医生问。
大肚山算不算?我上班的地方!医生笑了一下,接着说:「你血球的数量太多,也就是血液比较浓稠,怕会堵塞,有机会去捐血中心放放血!或者到血液科问问怎么处理会好一点。」
谢过医生,上了楼,原本阴雨的天气,已经转晴,阳光洒入医院大厅,突然有种还阳的感觉。
我心里无比感恩。
还好,仍能有梦,还好,仍有机会,去打造一个真实的自己。